2020-10-26 16:45:30
来源: 无
金华新闻客户端8月20日消息 记者 李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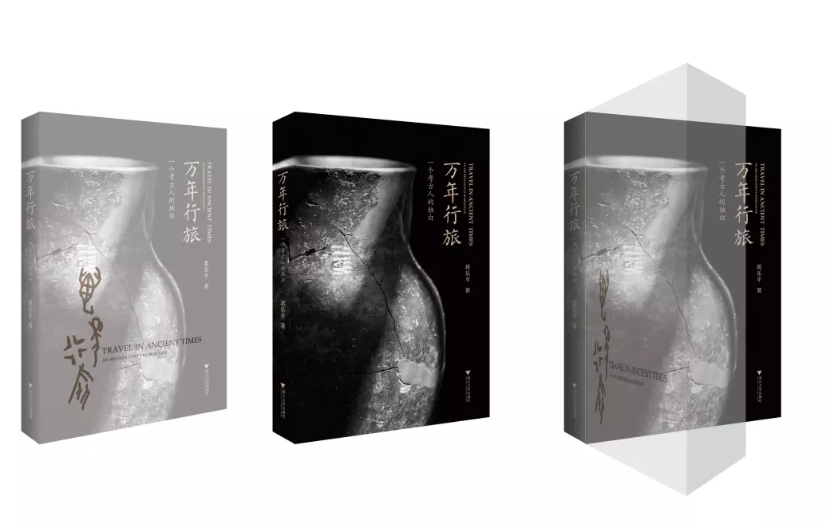

认识蒋乐平20年,知道他出书的消息着实吓了一跳。
那天,在上山文化研究和宣传工作群,向来低调的蒋乐平突然发了一条链接《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这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人生的新书推荐链。
记者纳闷不已,群里的人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没有人发言,除了浦江县委常委、浦江县委宣传部部长徐利民,他在读了几章,夸奖“朴实无华,写得好”后,特地留言“期待蒋老师新作出炉”。
过了一会儿,蒋乐平又发了一个新链接“《万年行旅:一个考古人的独白》问世”。
点进去一看,群里炸了锅。

天哪,居然是蒋乐平自己的新书链接。太出乎意料了——每天东奔西跑,忙得脚不着地的蒋乐平,竟然不声不响写出了14万字的书。
蒋乐平“羞答答”推介自己新书的方式,反映了他一贯低调、内敛的风格。
蒋乐平知识渊博,在现场介绍考古发现的前世今生信手拈来,通俗易懂。
记者和蒋乐平第一次认识是在浦江kuo塘山背的发掘现场,2000年,我初涉考古报道,小白一枚,连探方、灰坑等基本的考古术语都听不懂。蒋乐平不厌其烦,耐着性子一遍遍讲解。正因为蒋乐平的亲和力,原本对考古一窍不通的我,莫名地有了兴趣和好感。
浦江之后,我很久没和蒋乐平联系,直至2009年距今9000年的山下周遗址发现。
蒋乐平看到记者,感慨:“怎么你还在跑啊?杭州跑文物线的记者换了一拨又一拨了。”
记者在成文时,核实蒋乐平身份。没想到,近10年过去,能力有、影响有,蒋乐平却依然是我第一次认识他时的身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一直到现在,依然是。
蒋乐平不争,和谁争都不屑:他脸朝黄土,默默耕耘,收获一个又一个惊喜:浦江上山,义乌桥头,金华市区汤下周、青阳山、三潭山……
蒋乐平的身上鲜有荣誉、官职的光环,但他的踏实、勤励、豁达,却自带光环,让人读懂一名优秀考古工作者矢志不渝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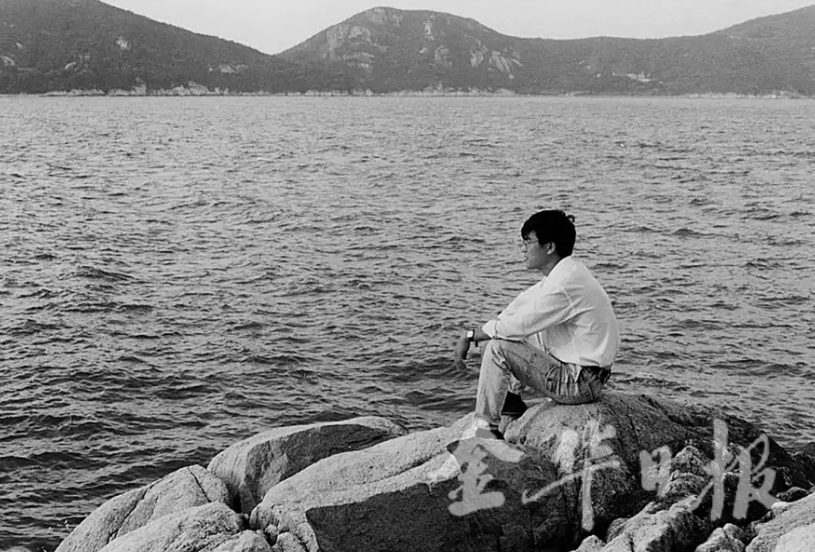

“从跨湖桥到上山,我亲历了浙江考古、也是中国东南地区考古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突破性一步。”
“上山遗址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河谷旷野型遗址,也是出现明确稻作遗存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一眨眼10多年过去。我有幸经常在上山遗址公园里漫步、参观。公园中的一草一木、一器一坑,都好似跳动着的生命体,向着我叙说它们的故事。 ”
……
蒋乐平是上山遗址考古第一人、国内外公认的上山文化专家,书中,他用大量的篇幅,回忆了其所带队的团队发现上山的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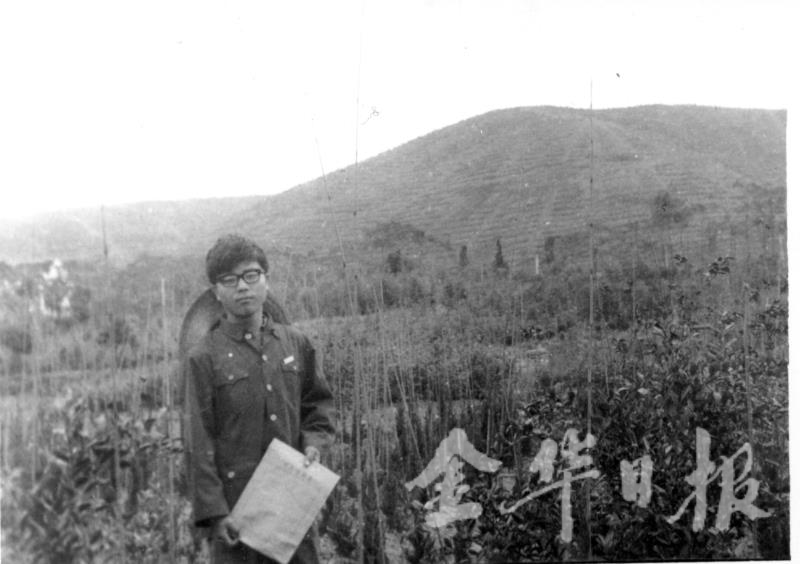
在“自由的乐趣”章节,蒋乐平写道:
2000年9月17日,我从诸暨乘班车去浦江。出发前,我与浦江县文管会办公室主任兼博物馆长芮顺淦通了电话,向他介绍了这次调查的目的和内容……他很热情,电话中介绍了浦江境内可能存在的遗址点,并让我乘班车在一个叫李源的地方下车。由于他的普通话极不标准,地名听得不清晰,客车达到浦江境内后,怕错过地址,我一路模拟发音向邻座询问李源的位置,方知李源并非一个车站。掐准一个岔路口下了车,终于与芮馆长会合……
芮馆长从李源带着我走向一个叫渠南的村子,也就带向了当时还一无所知、后来足以写入考古史的上山遗址。
蒋乐平还回忆了其发现跨湖桥遗址的经过,以及个中曲折。蒋乐平感慨道:“通往上山和跨湖桥的道路都经过了一个岔口。前者是一个叫做李源的一不小心就会错过的实在岔口,后者则是一个由复杂人事交集而成的虚设岔口。作为一个常年跋涉在田野的考古工作者,我的方向感其实非常差,但这两个岔口,都作出了无比准确的选择。”
各种机缘巧合,成就了上山,也成就了蒋乐平。

蒋乐平在书中如实记录了上山遗址发现在考古界带来的震撼:
2003年11月7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登《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
这篇报道社会反响,在不久后在桂林召开的“华南及东南亚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会议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成为了这次会议的“知名”人物。在分组讨论时介绍了上山遗址的发掘成果后,又作为重要报告在大会上作了宣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先生绘声绘色转达了浙籍考古学家吴汝祚先生得知上山遗址后的兴奋之情。可见国内外考古界对上山遗址发现的重视。

从那一刻起,上山遗址注定要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也从正从那一刻起,默默无闻的蒋乐平在考古界奠定了其在上山遗址发掘、研究无可替代的地位,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争相邀请他宣讲上山,蒋乐平把上山讲到澳洲,讲到美国,讲到世界各地……
霜如雪,
工地待日出,
又恐足下泥半截,
今日不得歇。
雨靴配阳笠,
考古队员称一绝。
刮地惜三分,
打探地层听消息。
这首作于2005年冬天浦江上山遗址发掘现场的打油诗,形象写出了考古工作人员不畏严寒、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当年,蒋乐平带队在浦江上山遗址发掘现场又增加了三个小探方,发掘在霜天雪地中向前推进。
这些考古的日常,酸甜苦辣,蒋乐平“万年行旅”的独白,却甘之若饴。书的后记,千言万语,化成沉甸甸的四个字:谢谢考古!


考古,单调、严谨,散文,活泼、灵动,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蒋乐平却完美地将两者合二为一。
浙江大学出版社在新书推荐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本考古人自述书。
我们来看看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跨湖桥、上山遗址的发掘者蒋乐平是怎么用“散文笔法”来概括自己的学术生涯的:
大学毕业整三年后,我正式开始了走向远古的跋涉:从七千年河姆渡出发,走过八千年的跨湖桥,抵达了一万年的上山。这是时间的逆行,这是思想的方向,这是考古人才能享受的旅程。
很少有人知道,工作有板有眼、轻易不苟言笑的蒋乐平“小时候做过作家的梦”,对一代文豪鲁迅尤其痴迷。蒋乐平写道:
阅读鲁迅,大致成了几十年中勉强称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自我标记。鲁迅让我视野狭窄,鲁迅让我的审美有了诸多的局限,鲁迅让我的文字佶屈聱牙……
记得大学期间和考古所工作的初期,同学和同事竟然都从我的文字中偶尔读出了鲁迅味,这曾经让我暗暗自得。
记者终于恍然大悟,每次发蒋乐平审稿,为何他总是能“容忍”记者考古之外抒情地有感而发,甚至还能站在记者的角度,认同记者跳出考古新闻化的标题,末了,还笑呵呵地来一句:“我知道,这样更吸引读者。”
蒋乐平从没掩饰自己对中文的兴趣。“我们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专业,文科只知道中文、历史、哲学,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考古专业。”
蒋乐平形容自己稀里糊涂地学了考古。当年,语文发挥失常,只考了70多分,不敢报考中文的他,就这样与考古结了缘。
前不久,湖南女孩以676分的高分,选择冷门专业北京大学考古系多次上热搜,在蒋乐平看来并不奇怪。
“北京大学考古历史上起码有两个以上省状元,我们那一届也有一个省状元选择北京大学考古,全县前三名的学霸,更是多了去。”
考古界藏龙卧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热情为本书作了长序:
我们的考古学家面对层叠的废墟,世代更迭,他会有莫名的伤感,这种伤感没有记录下来。
我们的考古学家面对森严的陵墓,面对某一代帝王,他对他会有话要说,有疑问求解,这些话没有记录下来。
我们的考古学家面对人骨化石,他也许会想到自己身后是怎样的,会去向哪里,千年万年又会是何人何时来研究我,这也没有记录下来。
……

我们的考古学家面对一颗颗炭化谷粒,一截截动物骨骸,会体味先人餐桌上食物的味道也许就变幻在自己的舌尖上,还要说道食饮姿势与礼俗的变化……
这一些,这一切,也好像都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
面对这一切,面对这千年万年的历史,我们怎么会无言以对,又怎么会无动于衷?我们时时都在思考,我们有许多的话要说。
考古学家,其实你有话要说,你要说出来。
……
蒋乐平透露,原本按照先前计划,等退休后,写一本回顾考古的小书。两个原因,一是生涯与一些重要遗址的发现联系在一起,写出来或许会有点价值;二是满足写书的愿望。这里所谓的书,至少属于随笔类,并非纯碎的专业书籍。没想到,各种机缘巧合,《万年行旅:一个考古人的独白》提前问世。蒋乐平随身携带一台笔记本电脑,或出差或返家,一年多断断续续地码字,这本书终于与读者见面。
上山遗址是怎么发现的?万年测年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叫上山?上山遗址和河姆渡遗址、跨湖桥遗址之间有什么渊源,这些问题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本报持续跟踪上山遗址20年,作为全国最早对上山遗址进行深度报道的记者,也是在看了书之后,才知道上山之名原来颇费周折:
上山之名来自何处呢?实际上,遗址一发现,我就准备给它取名。日记里最早称其为山背遗址,但山背与KUO塘山背有两字重复,而且后来了解到山背自然村并不靠近遗址,也就放弃了。渠南遗址也不确切,村里已经有了KUO塘山背遗址,有指代不明之嫌。但遗址所在高地确实没有小地名,怎么办呢?村支书老周看我为难,就说西北不远处有个“上山堰”,我想那就将就着叫吧,反正是一个代号而已。但上山堰会产生都江堰的联想,不适合称呼一个普通的史前遗址,因此就把堰字去掉,叫上山遗址。
当然,上山遗址的正式叫开,是在2003年之后的事了!
蒋乐平和上山的缘份,深深浅浅,均在《万年行旅》中深情告白,憋了一辈子的话,此刻喷涌而出——
发现上山,是平生最大荣幸!

更多资讯请关注金彩云
凡注有"金华新闻网"或电头为"金华新闻网"的稿件,均为金华新闻网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金华新闻网",并保留"金华新闻网"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