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26 10:27:46
来源: 金彩云客户端
我初中还没有毕业,家乡浦江已经沦陷了。我不甘于做亡国奴,就一个人离家往后方跑。
我过义乌、永康、东阳,到了缙云壶镇,才找到一所学校——杭州迁去的安定中学,收下我这个难民学生。寒假过后,从浦江到缙云,在义乌佛堂过铁路线的时候,被日寇的岗哨捆住了,就是不准过。我只得折回浦江,向西行。
浦江的西面是山区、山脉连互,人烟稀落。浦江到建德,虽然相隔只有120华里,行程却要两天。我背着行箧,拄着一根竹杖,翻山越岭上路了。
一路上很少碰具行人,就连荒村野店也没有,要过夜,就在废弃的山神庙,或者简陋的炭窑里。在那里兴许能碰见一些流浪人,可以一起说说话,问个讯。在浦江与建德交界的地方,有条岭,叫蛇家岭,名字很是吓人,我从来不敢在天黑时分过岭,六十年代我写过一个长篇,就是以这里作背景,一进入建德地界,虽然还有许多山丘,但比较起来,平坦多了。
过了一条江,到建德城了。建德是个府一级的大城。从前叫严州。比浦江要大得多,一些街道都是面板路,和浦江一样,很是古朴。
我到建德来,是为了我学校读书。但是要找到一所可供我这样一个流浪学生读书的学校是很不容易的。我首先看准的是建德的最高学府严州中学。我一次次徘徊在这向往和肃穆的殿堂般的校园门口,但就是进不去。我去报名,参加考试,都没有被录取。因为我小学毕业进中学后,日寇一次一次来侵犯浦江,学校办办停停,我转来转去,学习成绩低落,特别是数理化,可说没有学完过一本教科书。当时严中是个很正规的学校,我考试的分数差得很多。
我先寄住在建德城里一个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亲友家,天天早上捧着一本《升学指导》,做那些我至今也做不出来的数理化练习题。生记硬背那些并不太理解的公式。还有就是到民众教育馆贴报栏去看那种发绿发黄粗纸印的相隔个把星期的旧报纸。有时就在屋里写些习作,往那些抄来地址的报社寄。傍晚,我爱到城外的江边码头去,看熙熙攘攘的人群,摆渡过江,来来往往。也有人在江里洗澡和玩水,看见他们很快活,我也很快活。
后来,城里住不下去了。托人找到江对面一个村落里,住在一户人家。这家主人是一对老夫妇,孩子却比我还小,已经给他娶来一个二十来的大媳妇。
我在这家住了好几个月。除了温习功课之外,就是写作投稿。我写小说、散文、诗。往后方的一些报刊投寄。因为那时的邮路,要辗转绕弯,也不知是否能收到,收到了也不知是不是能采用刊登。即使刊登了,也很难收到样报。
我住在这农民家,写过他们一家人生活的小说《小丈夫》,寄到外地一家日报,就没有“回来”。
这年,浦江的几个同学,约我去淳安,报考淳安中学。谁知他们的减免费生的名额已满,根本不收战后学生。我们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只得原船返回建德。
回到建德,有位同学认识严中数学教师胡成英先生。胡光生是浦江人,我们就去找胡先生。那一晚,我们就睡在胡光生宿舍的地板上。我考不进严中,这晚上竟然能在严中的宿舍中睡一晚,心里感到一种满足,十分兴奋。现在想起来,那时真有一种强烈要求读书的饥饿感,驱使着自己努力上进。
因为我是严中的落第生,胡光生去查过我的试卷档案,不可能再进去,便写了一封信,要我去建德北方的骑龙桥,找浦江迁来的中山中学。
中山中学校长王恭寿先生,没有要我考试,答应我作为试读生入学。因为我缴不起半年一缴的学杂费和很大一笔代办费。我只能约几个穷苦同学住到离学校半里之遥的一个村庄的农民家里。
学校办在骑龙桥的龙庆寺,这个寺不小,共三进。前有小溪,后有高山。四周却无人家。风景大佳,也十分安静,是个办学读书的好环境。
中山中学的读书气氛很浓。一大早,莘莘学子,散在学校四周的田野小道上,各自专心朗读。
我所住的农家,只记得姓蔡。一位大娘,除给我们借住的学生做饭外,有时也会帮我们将衣被悄悄洗掉。这位大娘是很喜欢我们,手脚勤快。她为我们洗的衣服,还用米汤浆过,穿在身上很是挺括,还有一股米香,至今不忘。这位大娘如果现在还健在也是九十来岁的人了,和我的母亲年纪差不多。
我们住在她家的楼上,使用的是柏油的灯盏。我们在如豆的火光下做作业,看书自修。每天清早,便踏着阳光,沿村边小溪,听叮冬的流水声和另一边农田里的青蛙鸣声,去学校上课。中午回来吃饭,一天要走四次。我曾在这溪边小路上,和交错的阡陌间,吟咏自己写的歪诗,构思一篇篇的习作的故事。
中山中学虽然是从浦江迁来的,但浦江的同学是不很多的。除一部分来自桐庐,绝大部分是建德人。因为浦江、桐庐、建德都是速车在一块的邻近的三个县,生活习惯都差不多,大家都很合得来。
在中山中学就有个建德县城的叫杨国琐的同学,他也爱好文学,我们很要好。当时我写的一些作品,请他帮助看。我们离校后,还写过信。后来天各一方,也不知他何在,做了什么。至今留下深深的遗憾。
建德,给我很好的感受,我爱建德这块土地,我爱建德人。
我在中山中学没有毕业,因为一个误会,我被动退学了。
那学期,我在一次打篮球时,不慎遗失了一只戒指,这戒指并不是黄金的,而是银质的,它并非饰品,虽然不值多少钱,但这戒指面上却有我的印章。所以我一直戴在手上。不想因此而惹祸了。有一天,校长将我叫到办公室,说我给报社写稿攻击学校。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事。我猜想十有八九可能是我的印章落在谁的手上,有人冒用我的名字,给什么报社写了信。我办辩无效,就这样叫退学了。因为我还是一个试读生。我又失学了,又开始到别处去找学校读书了。
一天,我在建德城里,见到从杭州迁来的宗文中学招生。我去报考了。
我报考高中一年级新生。可是,我没有初中毕业证书。再说,数理化的试卷,我也做得不好。结果,名落孙山,没有被录取。
我很是失望。看来建德所有的学校,我都无法进去了。那时建德只有严中、中山、宗文三所中学。
不想,隔了一些日子,我又在街头看见宗文中学的招收高中插班生的广告。
我开始很迟疑,因为我考高一新生都没有能录取,怎么考得取插班生呢?
思想斗争了好几天,那几天整天像失魂似的,嚥不下饭,睡不着觉,就在民众教育馆报栏前面,江边码头上,走来走去。
最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即使百分之一百没有把握,我也要拼搏一下。
我去报名了,我索性报了最高一班:高三。
我抓紧学代数、几何、三角……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扑在复习上、一气坚持到临考的前一天。
考试那天,数理化大概能做出三分之一的题目,当然不会有及格的。但是那天的“作文”,我却发挥得很好。
我写的是我前几天在民众教育馆看过一位画家的画展。这位画家是杭州老画家斯道卿。斯老光生青年时代参加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军,辛亥革命时是他率部从清兵手中光复了杭州城。现在杭州这块土地沦于日寇。老画家是专画兰花的,但他展出的作品,所有的兰花,都是很不入土,显露于外,以示国土沦丧之痛。我在作文中大事发挥抗敌受国的意思,稿纸不够,另以添了三张白纸。
监考的老师见我一再索取白纸,十分注意于我,就立在我身后看我作文。当年,我年轻思维敏捷,富于激情,一挥而就,连标点也未更改。写完,这位老师就接了过去,当场看读。
不想,发榜时,我这个考不取高一的学生,竟榜上有名,考取高三。后来始知是这位老师,拿了我的作文卷,找到钟毓龙校长,钟毓龙校长看过我的卷子,同意破格录取我这个其他好几门功课都未能及格,而国文考试成绩特别优良的学生。
一进校门,这位老师是我们的国文任课老师,在他悉心指导下,我的国文水平大增。作文课上,我写完一本本的作文簿。老师的批语,也写得很详细。这位老师和我同姓,叫洪言讱,是建德人。
我后来愈写愈多,成为一个作家,不能不说到这位恩师洪先生和钟毓龙老校长,也不能不说到在建德求学的这段历史。
我在建德漂泊,上学,接触各种人物,和社会百态,我听到种种传说故事,都作下笔记。后来,我写作《神笔马良传时》,也用上了这些建德带来的资料。
我在宗文上课时,曾去方腊的点将台凭吊过,也搜集到一些百花公主(方腊义妹)的传说,我到过方腊起义地淳安,了解了那里的风土人情。我少年就想过写一部《方腊传》,还整理过一个写作提纲。
建德,是我从事文学写作的襁褓地,我从少年走向青年的第二故乡。我喝过建德的“乳汁”,建德也是我的一个母亲。
我进宗文不久,就传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很快,我就随宗文中学,沿富春江而下,迁返杭州。
我是在一个蒙蒙白雾笼罩江面,严东关若隐若现,大家的脸上充满喜悦的早晨,和建德挥手告别的。
离开时,我正是风华少年,一别经年,如今已是一个白发老人。
我深深怀念建德。我多么想,有一天再上建德这块美好而亲切的土地上看看它的新变化,和同学、故友们共叙别绪离情,一起回忆当年往事。自然,也会去看看建德的新一代,今天建德的中学小学的幸福而长进的同学们。
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写于上海。
编后记:
今年是一代文学大家洪汛涛先生创作经典童话《神笔马良》七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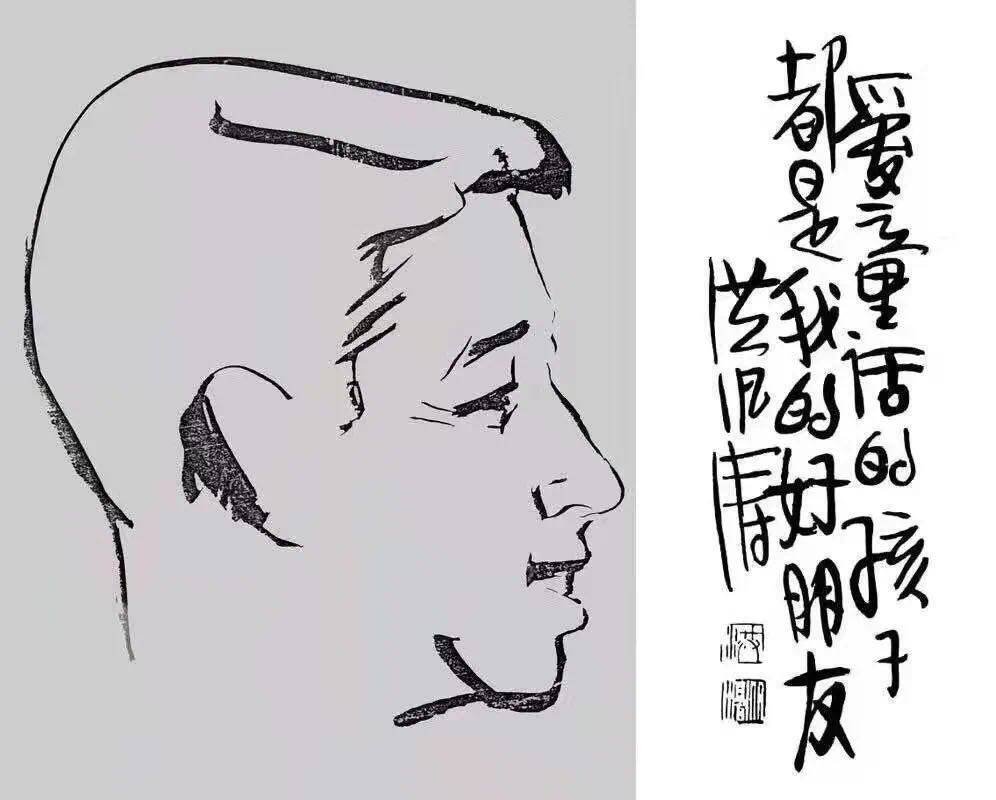
《神笔马良》是享誉世界的经典儿童文学名著,曾被编入教材,拍成电影、获五个国际大奖,是中国儿童文学难能可贵的瑰宝。
《神笔马良》也是从建德和宗文中学走向世界、走向辉煌的。作者在文中写的很明白:我在建德漂泊,上学,接触各种人物,和社会百态,我听到种种传说故事,都作下笔记。后来,我写作《神笔马良传时》,也用上了这些建德带来的资料。

更多资讯请关注金彩云
凡注有"金华新闻网"或电头为"金华新闻网"的稿件,均为金华新闻网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金华新闻网",并保留"金华新闻网"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