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30 07:00:05
来源: 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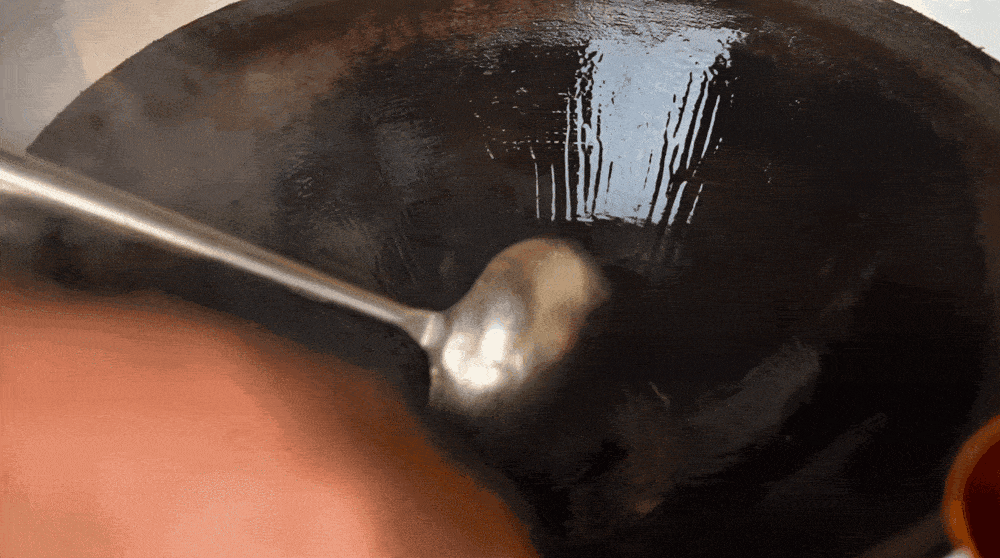
▲点击音频,一起聆听文章▲

作者:陆咏梅
诵读:孔 宸
华夏之臭菜最臭名昭著的数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浙东之人,将臭菜吃出天下香,是一绝。

多年前,行走在绍兴咸亨酒店的门前大街,满街飘散臭豆腐浓郁的奇香。晚饭时进食一道菜,才知臭豆腐之臭,真小儿科。那菜刚上桌,初看有模有样,淡淡酱色汤水,卧在白瓷盆里,错落有致、刀工匀齐、象牙白,与浙中红烧千张并无二致,主人介绍“霉千张”。落筷,起筷,谁想,千张不成条,没有顺筷子而上,筷头只沾一星半点,吃惊不小!入嘴,以为有腐乳的鲜香,谁知臭不可闻!抬眼看,满桌本地同仁,甘之如饴。
我,一个浙中人,不懂浙东人的舌尖惯性,恰如母亲不懂奶奶的口味。
奶奶一双三寸金莲,村中最数玲珑,奶奶因之风光无限。穿上尖头布鞋,行走如风,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奶奶年逾古稀,精明机警依旧,瘦削的身板硬朗,与高大伟岸的爷爷呈鲜明两极,一高一矮,仿佛高低杠。其实,爷爷都听奶奶的。力量强弱从来不会取决于肌肤骨骼的体积,而在于个体智慧技能谁胜算,爷爷的胃,拴在奶奶的厨艺里。
我们和奶奶分室而居,隔墙而住,分灶而食,比邻闻香。我和三姐,不如长姐二姐乖巧,受父母拘束少。奶奶爱养猫养狗,爱干净的母亲不沾奶奶的饭菜;奶奶爷爷嗜辣,母亲不吃辣,两口锅烧不到一块。
开饭了,一家子围八仙桌吃饭,我和三姐端起饭碗,一溜烟到了奶奶那儿。奶奶盘腿坐在高脚凳上,爷爷坐在一张方方正正的骨牌凳上。蹭菜之意全在辣,母亲厨艺极好,不搁辣,太寡淡。奶奶的饭桌一片红红火火,我俩辣得“吸溜吸溜”回到八仙桌边,立刻引来大姐二姐鄙夷的冷眼。她们觉得隔壁饭菜太辣,不及母亲做得精致,又或觉得,老人眼力不得劲,饭菜不洁净。婆媳过招,从来不用语言和眼神,靠的是几十年的厨艺功力。
但有一道菜例外,母亲与奶奶的嗜好一致——烂菘菜,婆媳默契无比。这菜奇臭无比,手若沾一星半点儿,立马渗入皮肤,洗刷半日,指尖指缝、手心手背依然臭味深长。臭熏十里,一开坛,大街小巷异味缭绕。母亲极小心,用勺子轻轻舀菜,手不沾汁。封坛前,取洁净抹布,将坛口擦得锃亮,不留蛛丝马迹,用牛皮筋扣住坛口,不留缝隙,才算圆满。然而,这抹布,需在池塘埠头汰渍半日,才能将异味消踪灭迹。

一坛奇菜,得之于十一月的白菜,白菜的水灵仿若江南女子,响当当的“菜中花旦”。白菜叶子青翠,色泽如春天嫩柳,长梗洁白如玉,纯粹无瑕。落霜前,浙中人将收割回来的小白菜去叶去根,独留掐得出水的菜梗,润洁饱满,切成半寸长,腌渍。成熟出坛,形体缩小,但色泽更温润,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亮。
若是一坛菘菜被遗忘,坛子里就有了神奇变化,那股刺鼻气味,汹涌而至。用手抓捞,触碰即化,那些鲜嫩爽脆的菜梗全成不堪一击的菜泥。细看,菜梗的丝丝缕缕被还原出清晰可辨的纤维,变身为浙中人眼中的烂菘菜。
奶奶和母亲,两位不同代的巧妇,用同一程序,烧出迥异的味道,只因母亲少用一味配料——辣椒。奶奶放油绿坚韧的青辣椒,色彩逼人,味道劲爆。舀一勺汤,漂着青椒,掺着白玉豆腐,暗黄色的烂菘菜汤汁便将所有的馋虫都勾出。

猪油熬香了,烂菘菜进锅了,锅里冒起无数青褐色的泡泡了。新长的辣青椒、新收的大蒜瓣、新切的水豆腐,一起入了锅,咕嘟咕嘟地炖,直到豆腐菘菜彼此交融。此刻的厨房,巷道里弄,飘满烂菘菜的香。趁着热,装盘装碗,汤汁浓浓稠稠,喜食者就着辣,抓起勺子就吃,越辣越带劲,豆腐的嫩、烂菘菜的鲜、青椒的辣、蒜瓣的香,各自相安,美美与共,边吃边冒汗。

昨日得了一袋烂菘菜,如获至宝,但那冲天的臭味,让人一言难尽。开车不到十分钟,满车厢奇臭如浊浪。到家后,将后备厢和所有车门敞开,驱散半天。然而,一入婆婆的手,便被拾掇得服服帖帖,那实打实的臭味易洗易除。
金华土菜馆供有烂菘菜滚豆腐,但不及奶奶烧的醇厚。
我的孩子随我,人在国外,一听说家里烂菘菜开坛,霎时勾起她的馋。“就好这一口”,是一股神奇的力量!即使口味水火不容的两拨人,都喜欢这道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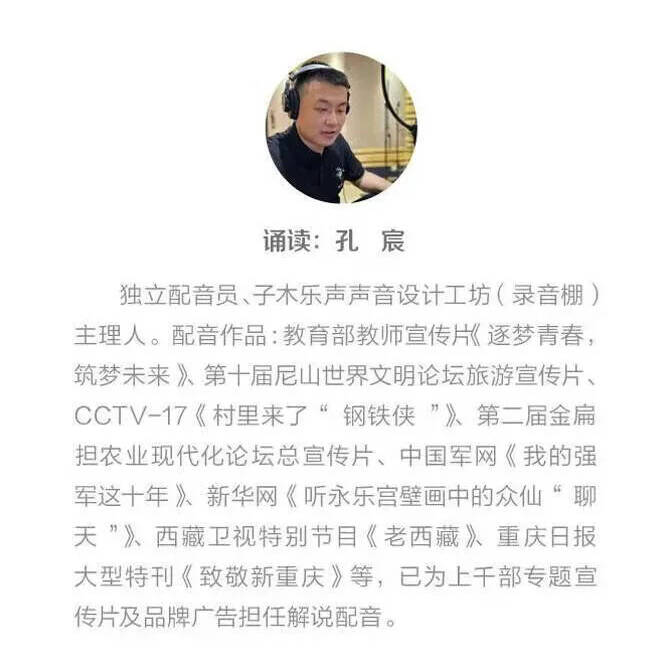


更多资讯请关注金彩云
凡注有"金华新闻网"或电头为"金华新闻网"的稿件,均为金华新闻网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金华新闻网",并保留"金华新闻网"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