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21 06:59:04
来源: 无


▲点击音频,一起聆听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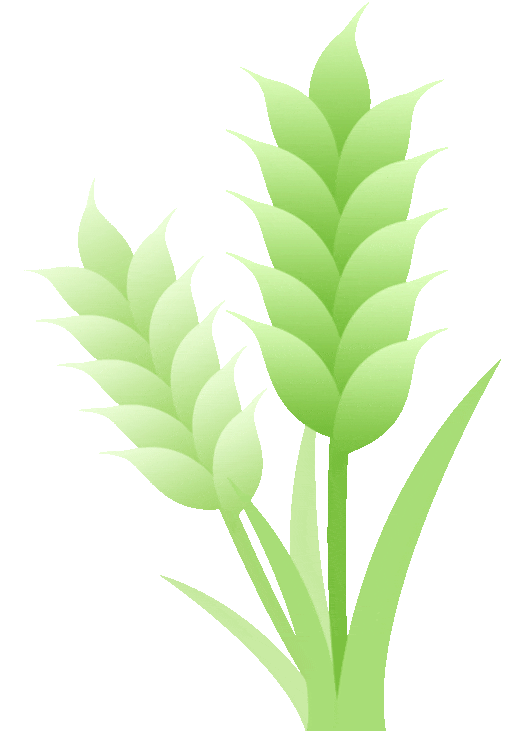
作者:赵国虎
诵读:陈盈盈
驾车沿武丽线翻过大庙岭,向东,在乡村公路的尽头,桑坑头就如一卷泛黄的册页徐徐展开。
四十多载光阴漫漶,山涧仍在石缝间流淌着琥珀色的光阴,涧水瘦成了一线银弦,在青苔斑驳的琴身上泠泠作响。石拱桥驮着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桥下两只水鸭拨开寒潭,涟漪轻吻着石壁的褶皱,恍若时光在岩层上镌刻的年轮。桥头老屋的窗棂间,悬着褪色了的辣椒串,门口两侧悬挂着的玉米棒也已褪作苍灰。竹排铺就的古栈道下,流水仍在编织着草叶的纹样。几只鸡掠过水泥路面,爪印踏碎了旧时蛮石街巷的跫音。道旁卧着晒太阳的那条黄狗,懒洋洋地站起身,问客:“你从哪里来?”只是当年挑山汉子的汗滴,已然化作苔衣深处的露珠,檐角的炊烟早已凝成云雾,悬在了毛竹林的上空。唯有山墙裂缝里探出的蕨草,仍保持着祖辈弯腰荷担的姿态。

这是我四十多年后的故地重游,记忆如老胶片般徐徐转动:腊月里腌肉缸浮着盐霜的咸香,火塘边煨烤着番薯的焦甜,雪夜中猎户皮袄上凝结的霜花,还有胜勇伯残缺的左手……
每逢农历二和七,是我故乡的集市。我家开有旅店,每到集市的头一天下午,我家的老屋便会宾客盈门,大多是桑坑头人。他们挑着山岭的脊梁,翻过十多里的山岭,再走二十多里的地,来赶第二天的集。卖掉木材或木制农具,或者是木炭、柴火等,再买些大米或者布料、生活日用品回去。然后还得走那二十多里的地,翻越那十多里的岭回家,生活好不艰辛。
我家的灶台从不缺公道,吃素念经的祖母的升斗,量得一年四季的风雨都服服帖帖。锅巴焦香勾我馋虫,祖母却说:“娃娃的馋嘴哪抵得过人家的饥肠。”经年累月,檐下往来客就成了座上宾,尤以其中的三位最为亲厚。正月里我随父亲进山拜年,蛮石街旁递烟筛酒的手,都曾在我家梁柱间留下过松脂香。

我少年时的桑坑头,早上家家户户炊烟袅袅,黛色的瓦背上热气腾腾,整个村子都像笼罩着一层薄雾。村子两侧的山头,更是云遮雾绕。因为是过年,太阳出来后,在村中那条用蛮石铺就的窄窄长长的山街旁,男人们三五成群,抽着旱烟,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女人们就在这山涧清澈的河水里浣衣,孩子们在街上追逐嬉戏,鸡鸭在觅食信步。
山里的年味总裹着腌肉的咸香。谁家梁上悬着整条的猪腿,必是腊月新宰的殷实大户。借肉还肉的习俗让邻里的炊烟都缠着情分,倒是崖洞里的红薯最解馋——炭火煨出的蜜浆,烫得人左手换右手也舍不得撇下。临别时,人们总要送我们几根杉木,那些带着年轮的馈赠,后来成了我姐姐的妆奁、兄长的婚床。
山里的天气要冷一些,但火盆总是红红的,暖暖的。那年正月初三,胜勇伯就着炭火讲述他的断指往事。火光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跳跃,残缺的左手举着铜烟杆:“眼镜蛇的毒牙刚扎进左拇指,我右手的柴刀就剁了下去了。”他轻叩烟灰,“咔嗒”一声,惊得炭星迸溅。我盯着他左掌根那狰狞的疤痕,仿佛看见一个年轻樵夫挥刀斩落毒血,猩红在雪地上绽成了寒梅。
胜勇伯伯已长眠在山坡上,野樱正将血色花瓣撒向涧水。他九十四岁的遗孀正坐在竹椅上拣豆,银发簪着山岚。她的掌心沟壑里,还泊着我父亲的名姓。说起当年“打办”搜查的险情,皱纹里漾开的笑意,竟比火盆里噼啪作响的炭星更亮。
暮色漫过车辙时,后视镜里缩成黑点的桑坑头,突然响起一声空谷回音。不知是旧时猎户的铳声穿越了时光的隧道,还是山风撞开了某扇虚掩的柴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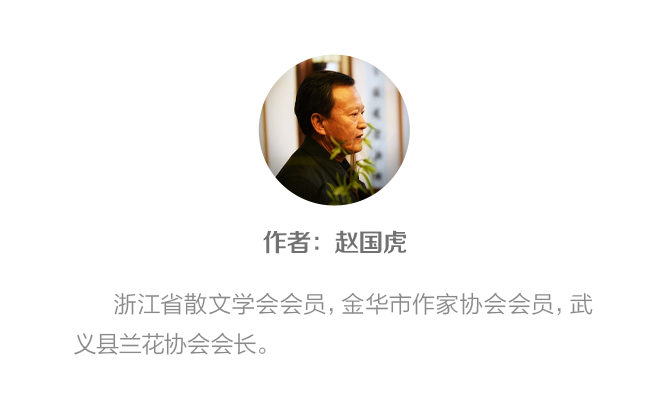




更多资讯请关注金彩云
凡注有"金华新闻网"或电头为"金华新闻网"的稿件,均为金华新闻网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金华新闻网",并保留"金华新闻网"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