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03 11:03:16
来源: 无
新闻从业30多年,我的采访对象成百上千,有省市县领导、上市公司董事长、身价过亿私企老板,也有如今仍活跃在一线的专家学者、影视明星,当然更多的是贩夫走卒。
“三教九流”自古有之,而且“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划分细致,据说到了元朝,没啥文化的统治者直接将臣民划分为以下等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好记易懂,简单粗暴,行之有效,“三六九等”的制度丝毫未变,依然散发着高低贵贱阴森森的气息。
往事越千年,即便换了人间,有些行当还是被烙上“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印记。比如“城市美容师”——“宁可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这个群体,社会美誉度极高,但有多少家庭会把孩子的未来与环卫工联系起来?
1994年7月12日,我在《金华日报》一版发表的《过路人对江“方便”煞风景》一文,开启了个人与环卫系统联系之门,从那以后,金华市环卫处是我采访过最多的跑线单位,没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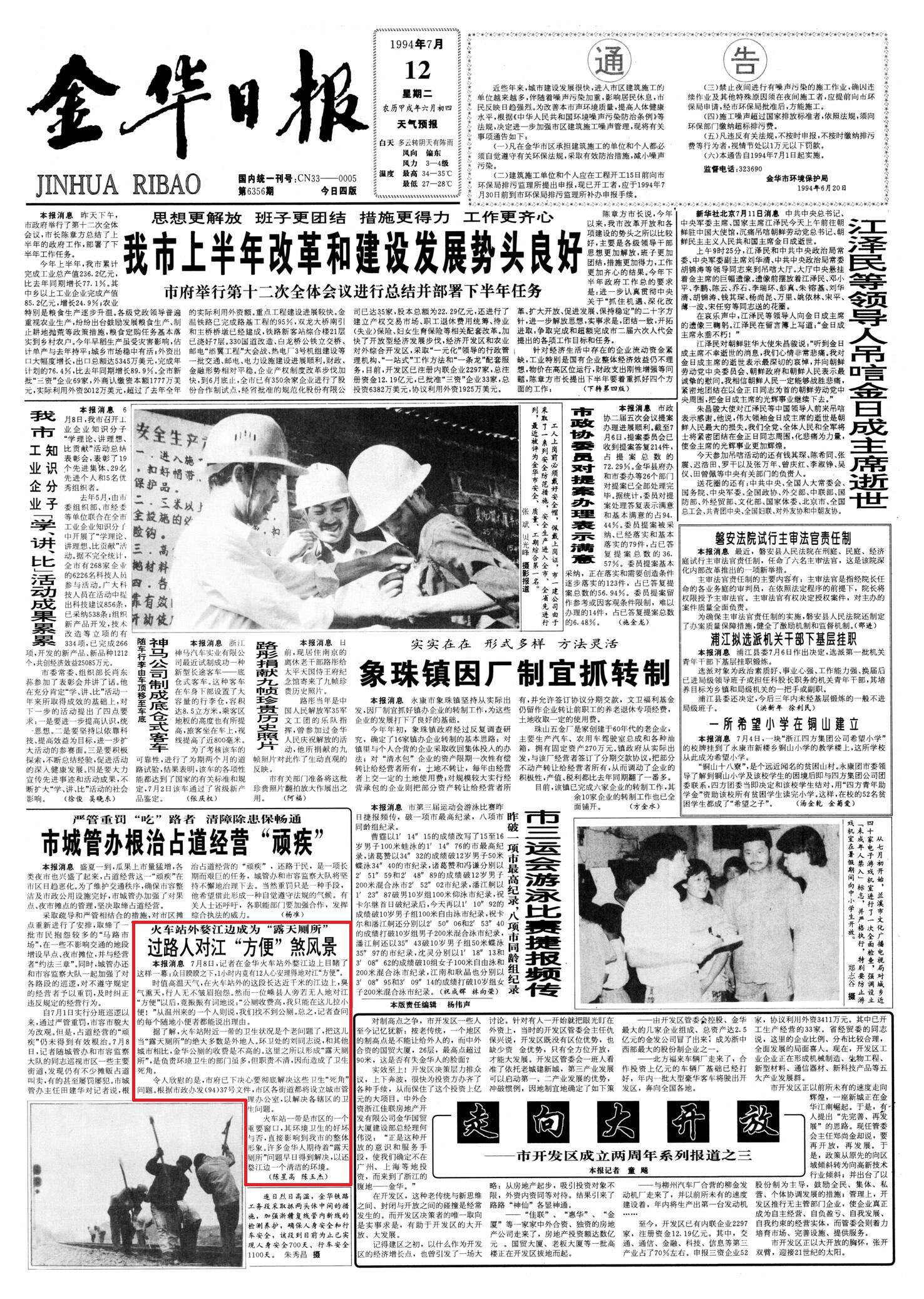
现在看来,因城市基础设施差、人们文明素质不高、法规不健全等而滋生的各种乱收费、乱罚款,是上世纪90年代各地的通病。在我的故乡蚌埠,火车站区域曾经出现过老头老太24小时不间断巡逻奇景,戴着红袖套的他们手拿罚款收据,目不转睛盯着那些抽烟、喉咙发响的人,一见烟蒂或者唾沫落地,说时迟那时快,伴随着断喝,他们已将收据递到眼前。好事者传言,某午夜,一男子走到暗处,解开裤子拉链作小解状,紧随其后的老太原以为逮个正着,不料该男子狡黠一笑,反问:“我又没随地小便,你罚什么款?”老太大惑不解:“那你干什么?”对方道出无赖真言:“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看看犯法吗?”
话题并未扯远,当时金华市区有35座公厕,在经费问题上捉襟见肘的金华市环卫处,不得不通过投标方式收取承包费。标的定下后,以为可以“发财”的竞标人纷纷抬价,但中标后如果按规定收费就亏大了。另外,那些不纳入环卫管理的“窗口”公厕收费更加混乱,如此恶性循环,使得“一号大事”问题频频见诸报端。

得益于《金华市城市管理若干规定》出台和20多年创建卫生城市、文明城市不松劲,金华变洁变美了,公厕实现免费。经历过这些变化的环卫人最清楚,人们卫生习惯没有养成之前,是他们硬生生用扫帚扫出的天下。

环卫人,对寒冬酷暑体会最深。盛夏,他们通过劳动竞赛给自己打气;除夕那天,他们一起过年,放下碗筷立马奔赴大街小巷……


翻看自己的新闻报道剪贴本,桩桩件件与环卫有关的事涌上心头……扪心自问,在这个许多人心目中不算体面的行业里,我有幸认识了不少值得交往一生的朋友,感谢他们在我最难过时候给予的帮助。

至于“环卫”与“丐帮”挂钩,不知何人发明,反正在环卫系统大行其道,他们自称“丐帮”,多少带些自嘲自立自强的意思。
耳熟能详的“丐帮”,自唐朝起即真实存在,通过金庸武侠小说发扬光大,“降龙十八掌”也好,“打狗棒”也罢,无不透露着生存的艰辛和顽强。
就像聊天群有千万种,金华的“老丐帮”与众不同。
如果说“老克勒”代表着上海人的考究和精致,那么金华“老丐帮”则传递着缘分与正能量。
这个群里的人,无论厅局级、县处级、乡科级还是教授、总经理、文艺工作者,无一例外均与环卫结缘,所以德高望重的群主一呼百应,“老丐帮”横空出世。
群主是一位为人极度自律做事非常低调的人,冷水洗浴不吹空调少碰油腻,在职时分管金华市环卫处多年,始终恪守“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他可以站在马路上声色俱厉批评环卫处科所队长工作不得力,但不允许他人对埋头清扫的环卫工人言一语。类似“看低不看高”的领导风格,怎么可能口碑不好?退休后的他,“一不做,二不休”:从不做给别人添堵的事,千方百计让自己忙起来——寄情山水超然物外,走八婺领略本土美景、去古都挖掘人文魅力、到国外探寻异域风情……
在他的影响下,在职时骑边三轮风驰电掣的王大哥,退休生活如同石子丢进水中泛起的涟漪,“运动圈”一圈圈扩大。他先从最小的圆圈开始行走的乐趣,每天爬尖峰山,接着骑自行车周游县市区,最远骑到江西、江苏,这几年迷上“穷游”——一个人,绿皮火车,经济型酒店,早上包子稀饭,中午拉面或快餐,晚上两三样小菜配半斤老酒。东西南北中、泰华衡恒嵩,与其问王大哥去过多少地方,不如问那个地方他去过多少次。这么说吧,春天里河南开封的王婆说媒正酣,含情脉脉目送王大哥离开,想不到几个月后“隔壁老王”又从洛阳兴冲冲赶来了。
吴大姐担任金华市环卫处“一把手”起码20年,到退休那天好像也没有“一把手”的样子。十七八岁时,她每天清晨到老城区的老旧小区居民家里收马桶,然后拉着板车吭哧吭哧将粪便运到集中点。几十年下来,人大代表、劳动模范等荣誉,被她换成一次次东奔西走,不遗余力争取资金提高一线员工待遇、新建环卫设施。她实在是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不管是谁,只要肯对环卫好,她认为好话说尽甚至低三下四都不是问题。退休后,吴大姐难改热心肠,常常到所住小区附近的十字路口义务值勤。遗憾的是,她的老伴、我们尊敬的姐夫前几年突然离世,让人再次愤慨“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那天,吴老举家迁往宁波前,吴大姐牵头召集部分“老丐帮”成员聚餐送行。看着她小心翼翼打开姐夫生前存放的好酒,我感觉鼻子发酸。
吴老籍贯安徽天长,说话带着南京口音,是金华城管(城建)系统的老处长,副团职转业,平时联系金华市环卫处,属于局领导、环卫处“一把手”的“中间人”。吴老好酒,有过“白酒一斤半,啤酒随便干”“若要问我酒量,手指大海方向”的豪迈气概,尤其喝到七八分时,他喜欢和我斗酒。我那时年轻气盛,加上王大哥插科打诨,于是酒桌变成战场,满杯白酒一口闷,然后啤酒连续“吹喇叭”。说实话,吴老酒量本在我之上,酒文化积累深厚,偏偏又会耍些花腔——像“更喜岷山千里雪”,他不但能改为更贴近现实的诗句,还将“雪”摇头晃脑念出莺啼燕啭。面对常常败下阵来的我,王大哥总会揶揄“这个团副太狡猾,你个士兵怎么能干过他”。吴老一直不恼,骨子里忠厚的人啊。
同为安徽老乡的董主任,是我当兵时另一连队的指导员,转业几年后接了吴大姐的班。每次和董主任小聚,我都会瞎想,要是在部队时彼此这么熟络,讲义气的他应该想方设法让我去圆军官梦。董主任温文尔雅,嫂子善解人意,那次几个老乡参加家宴,两个人忙活半天,端着一个个热菜走出厨房,发现迫不及待的我们,居然就着凉菜已经喝醉了好几个。就算这样,董主任也不含糊,三下五除二补齐该喝的酒不说,还带着我们大冬天去尖峰山脚下的水库游泳,现在想来后怕之余,更加怀念那些纯粹时光。
论酒量,“老丐帮”里吴老、董主任不算牛的,省建设厅、市建设局的处长,浙师大、金华银行的老总,还有陆兄、梅兄、方兄……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有“几把刷子”。而群主、徐书记等不少人,几乎不怎么碰酒。这么一个“酒不同道却合”的聊天群,几年来生命力不减的原因,除了不吵不闹不发广告,无疑靠特定群体情感支撑。
是的,“环卫”让我们相遇相识,“丐帮”使我们相聚相知,金华的街头巷尾,有我们共同的温馨往事!

更多资讯请关注金彩云
凡注有"金华新闻网"或电头为"金华新闻网"的稿件,均为金华新闻网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金华新闻网",并保留"金华新闻网"的电头。